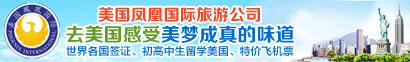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去世,享年百岁,我称他“方伯伯”也已超过一个甲子。他与先父张高峰是总角之交,既是中学大学同窗,又是新闻界同行,有过半个多世纪的情谊;我自幼就知道他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直至我也年近花甲,仍不时得到他的教诲。送方伯伯大行,记述我知道的二三事,以飨读者并寄托哀思。
半个世纪的情缘
方成本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论起来还是孙中山先生的族人。方成的祖父很早就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父亲在平绥铁路(北平到包头)局做职员,因此他出生在北平,一生除了小时候回乡,读大学在四川,短时间辗转上海、香港外,在北京生活了80多年,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
1933年,方成考入北平弘达中学,与同龄的张高峰成为好友。1937年,北平“七七事变”,华北沦陷,抗战爆发,方成与张高峰分别南下,一个休学回乡,一个从事抗日宣传。方成1939年北上入川,到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就读化学系,张高峰1940年以同等学历插班入读武大政治系。好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虽不同系,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演话剧、出壁报,再度同窗生活,并且同于1942年毕业。方成到距乐山不远的五通桥黄海化学研究社工作,张高峰被重庆大公报派往中原做战地记者。1944年中原会战后,张高峰回到重庆负责川西报道。“黄海”是著名的“永久黄”化工实业团体,张高峰多次采访,每次必去看望方成。方成保存至今在“黄海”的珍贵照片中,就有他俩与另一位同学张荣善的合影。1981年,张荣善从美国回来探亲,三人欢聚,还特别以当年同样的位置合影,成为跨越37年的一段佳话。
1946年,方成到上海重谋生路,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绘图员,后来才走上以漫画为终生职业的道路。当时,张高峰做大公报记者,方成说,“我的第一幅见报漫画,就是经高峰推荐发表在北平新民报上,后来又推荐连续发表在上海大公报。《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看到了,聘我为漫画版主编和特约撰稿人。”“方成”这个笔名也是那时开始使用的。“我妈姓方,‘成’字好写,两个字的笔画都比我本名少得多。”方成的解释就这么简单。
1949年,方成从香港回到北京,步入新闻界,与张高峰成为同行,联系更密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报与人民日报宿舍都在永安路上,我们两家仅一路之隔,甚至孩子上学都在同一学校,自然过从甚密。记得三年“度荒”时,家里伙食有点改善,父亲就会吩咐我们“去喊方成来。”(他似乎从不说“请”)
永安路的那段日子,是我父亲与方伯伯来往最方便的一段时光。“文革”中,他们都未能逃脱厄运,彼此通信也只能互勉保重。1972年,在河南五七干校“改造”的方成还专程跑到天津,看望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做了农民的张高峰。说来诡异,方成下放的地方正是张高峰1943年写披露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的叶县,大公报因此被罚停刊三天,张高峰也被当局逮捕。斗转星移,30年后,方成又在此“遭难”,冥冥之中他俩真是一对兄弟。
“文革”结束,他俩双双恢复工作,虽然分处京津两地,但书信往还,互通信息,从未间断。彼此工作有需要时,必相互帮助、合作,有机会还要欢聚小酌。他们偶尔也会谈谈家事。1981年,方成回乡探亲,来信说,他那连面都没见过的祖父被“摘掉”了“地主帽子”,村支书说他家的成分实为侨工,“但我已当了30年地主的‘孝子贤孙’,并挨了批也写了不少思想检查。”
我父亲晚年多病,几次住院。方伯伯知道老友在拼命般地写作,每次来信都会叮嘱他注意休息、保养,来日方长。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到天津探视,两人还曾抵足而眠,彻夜长谈。1989年春,我父亲病重,方伯伯又一次从北京赶来。他是父亲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位同窗好友。那天,我送方伯伯回招待所休息,他在路上谈起与我父亲的友情,感叹好友命运多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父亲去世后,方伯伯又把那些话写进了文章,可见情深意长。他写道:
“我和高峰是莫逆之交。他交友是真诚的,而且是持久不忘的,他走到哪里都会有朋友,都能够找到帮手。对高峰来说,新闻事业和亲友之情,是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然而并不限于私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说来惭愧,我缺乏高峰对友人那种拳拳不忘的深情。······高峰对新闻事业孜孜以求,万难不变,至死不移的精神,在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是罕见的。······高峰的死,使我深感痛伤,难舍的是他那样深情的友谊,加上对他怀才未尽,天不假年的惋惜。”
方成的艺术道路
方成最早画画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父亲说他上课时就喜欢在本子上画“小人儿”,都是古典小说里的人物。1935年他们参加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时,他就负责画抗日宣传画。方成画漫画起步于武汉大学。当时,武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演话剧、办壁报是方成与张高峰共同的爱好。其中“黑白社”出的壁报,每期都有方成署名“利巴尔”的幽默漫画,反映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景,连宿舍里跑老鼠、捉臭虫都“入画”,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鲜为人知的是,方成在黄海化学研究社四年,虽然工作是化学实验,却没有放下画笔,画了不少人物肖像速写,包括范旭东、侯德榜、孙颖川,现在都成了珍贵纪念。上世纪80年代,张高峰编撰《化工先导范旭东》一书,就是把方成当年为范先生画的速写做了封面。1943年11月间,冯玉祥先生到“黄海”参观,方成当场画了一张速写送给他,冯先生说:“礼尚往来,我也画一张送你。”遂画了三个并列的辣椒,中间是绿色青椒,两侧是红色长尖形海辣,并题诗曰:“红辣椒,绿辣椒,吃起来味最好;大家多吃些,定把倭寇全打跑。”冯玉祥行伍出身,靠自学通文墨,能写能画,还是人们交口称誉的“丘八诗人”。周恩来曾说:“丘八诗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那首《辣椒诗》中,冯先生把抗日战争的艰苦比做吃辣椒,教诲年轻人,坚持下去就能打败日寇。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方成家还看到那幅画。他说:“‘文革’中我所藏的许多名人字画都被毁了。由于这幅画不大,夹在书里没有被发现,整理残局时才找出来裱好,很怕被什么纪念馆知道后要去。也曾有人建议我写文章和发表这幅画,我都没有照办,因为它很珍贵,我实在舍不得送人。”后来,方成把自己的大部分收藏都捐献给了家乡的博物馆,我想,也应该包括那张冯玉祥先生的画吧。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方成主要画连环幽默漫画,单幅作品少,但风格开始逐步转向讽刺,主题包括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他后来避居香港,就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在香港,他画表现市井生活的四格漫画,每天要跑出去观察社会生活,发掘生动细节,触发感想,融入作品,这也成为他后来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
1949年,方成步入新闻界,主攻国际新闻漫画,名噪一时。偶有讽刺作品,难免“引火烧身”,直至“文革”中被诬陷、搁笔。浩劫过后,方成的一幅《武大郎开店》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漫画佳作,从此再次进入创作高峰期,并且频繁巡回办画展,开讲座。他把国画水墨技法引入漫画创作,兼写杂文、评论,后来更转入幽默与讽刺的理论研究,不断出版新著。这些成就多有介绍,不赘述。
人们不大关注的是,方成夫人陈今言曾任《北京日报》美术组负责人。她毕业于辅仁大学,学的是油画,后来又学漫画、版画,还对工艺美术发生了兴趣,是我国美术界少有的才女。当年永安路宿舍里她制作的小工艺品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陈阿姨是大家闺秀,端庄贤淑,参加革命很早,为人刚正不阿,却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身心俱疲。1977年夏天,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舒心的日子刚刚开始,她竟在上班途中突然发病,抢救不及猝然离世,年仅53岁。
养生“秘诀”与达观心态
方成有一首打油诗广为流传,诗曰:“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这是他对自己生活的生动写照。
熟悉方成的人都知道,他酷爱骑自行车。爱到什么程度?说一件我经历的事。2002年,方成84岁。一天,我给他打电话说,哥哥姐姐多年没见您,我们准备一起去拜望。他说,你们不要跑,我骑车过去。你们报社的路我熟。(他常来我供职的报社参加漫画评比、座谈)我一再劝阻,但他坚持,说骑车也是锻炼,还加上一句“上车就有座儿”。我笑着只得依从。那天,方伯伯从金台路骑自行车到北二环安德路,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其实,他走路也很快,记得他70岁时与我同行,我要加快步伐才能与之并肩,而我的年龄仅及他半数。
方成很忙,为什么要忙?忙到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我父亲聊天,说到访问日本的感受,特别提到日本人的讲求速度和效率。他说,“文革”耽误了我们十年,少做了多少事情啊。我们这一代再也耽误不起了,要抓紧时间做事情,还要从头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譬如关于幽默与讽刺的理论问题,过去没有人研究,我很感兴趣。学点新知识,做点新事情,也是一种自我新陈代谢。后来,他给我父亲的几封信中也一再说起同样的话题:“······兄多保重。我们虽然都是小人物,但也是国家财富之属,多干一年是一年为后人多留些遗产。”我“每天从早晨六点多起床,到晚上十一点,除有人来或有非看不可的电视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之外,几乎都在工作,包括假日。”“人有了一点名气,来找的人和事就多了起来,其实生活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朋友间的情谊和鼓励、工作中产生出对人民有益的成果。”“现在真得快干,加紧干了,时间太不够用了。”为了快干多干,耄耋之年的他居然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方成很达观,也很坦诚。他住了20多年局促的宿舍,画室不过十多平米,一张画案占据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空间,加上小沙发、茶几、餐桌,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画稿,给人印象乱糟糟。方成却说,乱中有序,他自己能够找到需要的资料。由于空间有限,写作、画画常常要挪开许多东西以腾出地方,甚至打开折叠小餐桌才能落笔。画室兼书房,连会客、吃饭,方成戏称“多功能厅”。但他同时“声明”:“我能随遇而安,虽然心里并未以此为乐——我还没有那样的涵养。”
大凡名人,多忌讳自己曾经不大“光彩”的事情。方成不然。譬如,有人说他当年从香港到北京,赶在开国大典前参加工作,获得离休待遇,是“有觉悟”的体现。方成却坦言,他本来是想回上海,结果轮船不能进港,靠朋友帮助又上了到北京的船,没想到与许多民主人士同行,到北京后靠朋友很快找到工作,又“意外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说,这是“赶巧了”。又如,说到自己“政治上不进步”,又不得不“讲政治”,他对自己曾经与落难的朋友“划清界限”,未能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一一道来,毫无隐讳,并说,“这些亏心、对不起亲友的事情,在我心中一直是沉重的块垒,使我终生不安。”
2011年元旦前夕,我去看他。见到老友的孩子,不免说起往事,每每引得大笑。他说,中学时自己的志向是当医生,但投考燕京大学医学院落榜,“老师说我智力测试不及格。”谈到当年从“黄海”辞职,他说,若不是因为失恋跑到上海,我就成不了漫画家了。说起自己92岁还能参加广州亚运会火炬接力跑,他颇为自豪。我问他养生之道,答曰:一要活动,每天锻炼;二是用脑,每天写文章。又突然冒出一句:世界上假的东西都可恨,只有一样是好的——假牙,“没有它我活不了。”我祝他长寿,他说,对,上不封顶!又是大笑。方成确实是幽默大家,而达观与坦诚,是他心胸开阔,得以高寿的重要原因。
追忆方伯伯,思绪绵绵。想起当年他写给我父亲的祭文,就用其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他悄然离去了,却非无声无息,怀念他的人不知多少!每看到他留下的发表在众多报刊上的篇章,就会在人们心中浮起他那不知疲倦、长年奔波的身影,和幽默动人健谈的风姿。他是令人难忘的。”(文、图 / 张 刃)
(责编:段晨茜、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