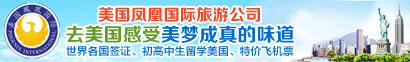邓友梅未搬家时,与我住同一栋楼的同一层,窜门唠嗑,捎书带信,抬脚就到,推门就进,是名副其实的近邻。
大概是1999年1月吧,老邓到我家,问我富贵竹多少天换一次水,液体肥料怎样用?那几天,我正应约写一篇文章,但一直写不好,换了几个开头,改了好几遍,还是不顺溜,只好放下,搁搁再说。我对老邓说,写东西算起来也有些年头了,书也出了几本,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很是苦恼。最近,我翻出一堆书,有你的《闲居琐记》、《无事忙侃山》、《烟壶》、《京城内外》,还有汪曾祺、孙犁、陈建功、贾平凹的东西,细嚼慢咽,咂摸滋味,想学点本事,有点长进。
老邓说:“汪曾祺的东西很讲究,但不留痕迹,表面上给人以轻松随意的感觉,其实他在肚子里反来复去不知过了多少遍,每个字都经过推敲琢磨,才落笔成文。林斤澜的文章,也有特色,甚至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但他在那儿琢磨来琢磨去,煞费苦心,改到最后,反倒有点涩,读起来不那么顺溜了。建功的语言独特,有一股‘嘎’气。贾平凹的东西,也有嚼头。写作没有什么绝招,还是老话,多读多写,功夫怕有心人。找你喜欢的古文,或与你风格相近的文章,多看几遍,多背一些,肚子里有了东西,下笔时就会自然流露岀来。我背过《楚辞》、《聊斋》、《红楼梦》中的一些章节,学习人家叙事状物的简洁。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老舍先生领导下工作。我们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点评,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在草叶上变成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飘到山顶,浮在空中……写完后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你别瞎搅和。有一回我问老舍先生,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文章总是疙疙瘩瘩?我应该怎样改进呢?老舍先生说,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已先大声念两遍。你念着顺口,不打奔儿,别人看着也就顺溜,要是自己念着都跟绕口令似的不顺嘴,结巴别扭,人家看着也决不顺眼。这点教导,我受用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仍关上门大声念两遍,碰到绕嘴的地方,坚决改正。一个作家,不注意语言修炼,话都说不顺溜,怎么能写好?”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教你一招,用大话说小事儿,用小话说大事,效果奇佳。我说,姜白石也说过类似的话:“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二
2004年2月,潘芜老师从长春寄来两本他的新作《艺文碎片》,附了一封信,叫我代他送邓友梅一本,还说老邓的书,他差不多收齐了,只缺香港版《散文杂拌》,不知老邓手头有没有,叫我去问一下。
去年8月,我请老邓去我的故乡——吉林省乾安县,参加大布苏文学研讨会,邂逅潘芜老师。潘芜少年成名,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我县文化馆,辅导文学爱好者写作。我那时是中学生,在潘老师主编的《街头文艺》上发表过散文、小说。我对老邓说:“这位是潘老师,我文学的启蒙人。”老邓说:“常听喜儒说起您。”他们站在在大布苏泥林的苍茫暮色中聊了起来。我看着这对位年龄相近,经历相似的难兄难弟,感叹唏嘘:他们都是寒门子弟,少小离家,参加革命,学习文化,成为作家;他们都是风华正茂时,被打成“右派”,落难蒙辱,妻离子散;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平反复出,恢复名誉,重返文坛……
我知道潘芜老师爱书如命,是吉林省著名的藏书家,不敢怠慢,马上拿着书去找老邓。老邓说:“那书是前几年出的,让我找找看。我现在总忘事,你也帮我记着点,时不时地提醒我一下。”
他刚从桂林回来,显得有点疲惫。他说今年天旱,漓江的水很浅,有时船底会擦着河底的石头,走得很慢。漓江岸边,蓋了许多房子,与我们二十年前去时,大不一样了。1983年,我与老邓陪日本作家水上勉一行去过桂林。那时的桂林,如诗如画,令人陶醉,我在游船上,给日本朋友翻译了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老邓感叹道,旅游点,不能开发一个,糟蹋一个,要想方设法保护好生态,眼睛不能只盯着钱。
闲聊时,我说,你的文章很少用成语、形容词,文字干净利落,连一些枯燥的应景文章,也写得不落俗套,有滋有味,这本事是怎样修炼的?老邓说:“我受汪曾祺影响很大,他说写文章要干净,一个句子,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多用。我写完文章,花很长时间,很大精力,一字、一句、一段地琢磨,一个字能说清的,绝对不用两个字,这样写长了,养成了习惯,下笔时自然就干净了。文章写完后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下苦功夫。别人说过的话,最好不说,非说不可就改个说法。光熟悉生活还不行,还要有表现生活的特色语言。中短篇小说的文字很讲究,那怕只有一句废话,一眼就能看出来。汪曾祺说,笔墨简洁干净了还不行,还得艺术生动。他的散文,都是大白话,但那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大白话,就像掐头去尾的二锅头一样,看着跟白开水差不多,其实是酒,醉人。我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词比较抽象,用多了,反而絮叨。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导师是张天翼。他教导我说,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不说漂亮这两个字,你只写她的形象,让人读后感觉她真是漂亮才行。你想骂一个人,但不骂他,写出来让人一看就觉得这家伙真不是人。这才是真本事。我喜欢直来直去,单刀直入,这样文章才能嘎巴溜丢脆。我认识一位作者C君,写了一辈子,一直没长进,还是中学生的语言,教科书上那一套。还有位L君比他好些,但成语形容词罗列太多,读起来罗嗦絮叨,很不舒服。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文字都要讲究。以前听萧军说写小说是年轻人的事儿,我还不信,但现在我信了。小说需要想象力,琢磨结构、情节、人物性格,我现在写起来就感到吃力。到了一定年龄,精力不济,写些散文比较顺手。现在有所感触,就写散文。散文没故事情节,靠什么抓人?只有语言。而语言要炼到火候,没有几十年工夫是不行的。”(上)(文、图 / 陈喜儒)
(责编:段晨茜、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