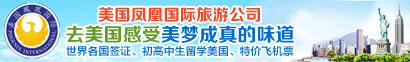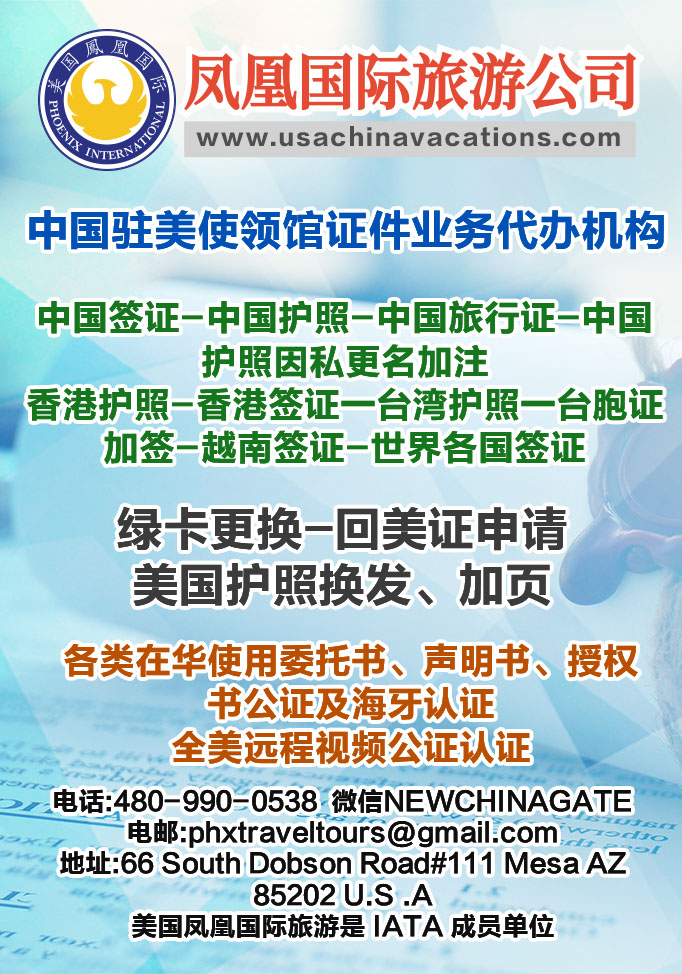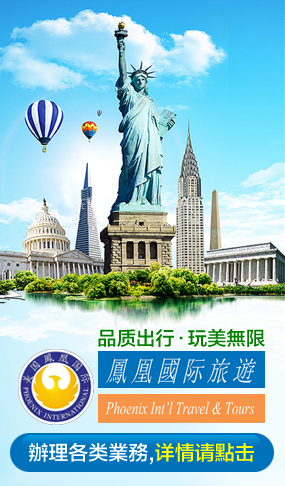中评社香港11月26日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沈雅梅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当前中美互动升温的背后》,作者认为: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美高层交往重启,互动升温,双边关系出现止跌企稳的迹象。事态表明,尽管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已定,但中美仍有共同利益,能够找到和平共处的方法。这背后,对年内可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预期是重要驱动,同时也存在其他有助于关系稳定下来的结构性因素。尽管如此,仍要接受高层互动并不足以从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的现实。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2024年大选周期前后,中国议题仍会被炒作,谈判进程与合作进展均可能被否认或推翻。文章内容如下:
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美高层交往重启,互动升温,双边关系出现止跌企稳的迹象。这是对今年初“无人飞艇事件”以来中美关系遇阻状态的纠偏,是两国落实巴厘岛元首会晤共识的延续,也是在双方对彼此的政策都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实现的。这轮互动升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1月即将举行有中美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这一预期的驱动,为稳定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现在距离美国2024年大选季已经很近,在两党已有“对华强硬”共识的背景下,美方几乎没有时间把对华接触与合作推向深入。因此,关系向好的势头恐怕难以解决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值得探究的是,有哪些因素是中美互动升温的持续性动因?它们是否足以催生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态势?这将有助于中美关系在可预期的未来抵御下一次危机的冲击。
一、辩证看待中美互动升温的态势
中美高层互动增多,合作可期,分歧可控,气氛有所缓和。但美方对华姿态的调整是策略性的,并非战略性的改变,因而不会对中美关系总体局面带来实质性改善。
第一,互动增多。6月至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气候特使克里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两党议员代表团等多批次高官访华;韩正副主席出席联大会议时与布林肯、克里会谈;王毅外长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战略沟通;中国领导人还在京热情会见美国企业界、民间团体和前政要等。这些走动大多数是自疫情以来的首次线下活动,促成了两国官方定期对话的恢复,也带动了民间交往的活力。作为此轮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巴厘岛元首会晤共识的落实,两国建立了新的机制,包括财政部门间“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开辟了新的沟通渠道,即成立中美商务工作组、启动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举行保护商业秘密专家磋商;并在近期举行亚太事务磋商、海洋事务磋商、外交政策磋商。各层级交流起步,内容涉及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及亚太地区形势,议题逐渐具体、深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回暖”的期待。
第二,合作可期。对美国而言,“接触”作为一种对华政策范式已经失败和结束了,但作为沟通手段和互动方式仍是现实需要。拜登政府在锁定对华竞争的同时,保留了选择性合作的要素,以此凸显“负责任地管理对华竞争”。这与共和党保守派主张对华竞争就意味着不接触、不对话有很大不同。拜登执政一年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词就从“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①变为“投资、结盟、竞争”三点论②,去掉了“对抗”的字眼。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双轨合作”模式,其中一条轨道是指美国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进行建设性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共同挑战则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经济动荡等”。对中国而言,这类问题公益性强,攸关国际社会福祉,是一个大国理所当然的关注。全球气候治理也是中美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关系的重要内容。截至2023年7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克里已会面53次,双方保持气候对话与合作,释放出两国严肃应对人类共同威胁的信号。
第三,分歧可控。拜登政府认定中国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主要挑战;同时表示要“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反复称要为中美关系建立“护栏”和“筑底”。这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聚焦于分歧、争端和危机,把中国作为对手甚至敌手的成分上升。对美方而言,“管理竞争”或管控分歧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战略意图:一是为了防范危机升级失控,打造对华竞争的终极保障;二是降低中方的威胁感知,诱导中方做出符合美国偏好的政策选择,限制对美反制能力;三是缓解其他国家对中美竞争、对抗和冲突的担忧,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拜登政府一再作出“四不一无意”“五不四无意”等口头承诺,可归入“管理竞争”的一面。③沙利文提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是“去风险”和多元化,而不是“脱钩”,是把原先针对中国的话术,改变为针对中国所处环境的话术,有意减少对抗色彩,也属于“管理竞争”。这与中方希望通过管控分歧来稳定中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关系的目的有本质区别。
第四,矛盾难解。美方通过调整策略,使用“谈打结合”“软硬兼施”、言行不一的办法来推进对华竞争和控制竞争烈度,其对华竞争的战略底色没有改变。尤其是美方始终推进对华科技“脱钩”、干涉内政、战略围堵,导致中美关系的症结问题突出,矛盾难以解决。一是美国对华科技战不断升级。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模糊“军民两用”界限,加码对华制裁和出口管制,瞄准高科技、投资、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等,打压中方优势产能,为中国科技发展“限高”。据美商务部数据,截至2023年5月31日,被列入各类清单的中国实体有近700家,其中超过200家是拜登政府时期新增。2022年,中国出口许可证的申请数量同比下降26.2%,平均申请时间由2021年的76天增加至90天,远超其他国家43天的平均用时。④
二是美国涉台政策发生倒退。美方打“台湾牌”的意图很多,包括以台湾为地缘政治制华的桥头堡、“民主化”战略的盟友、“芯片联盟”的产业基地以及利用在台海生战生乱、铺设中国崛起道路上的“陷阱”。这决定了美方将长期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挑衅和战略消耗。行动上,加强对台军售和供应链联系,提升官方待遇,给予外交支持,弱化对所谓“台湾主权”和“协防台湾”的“战略模糊”,不断掏空一中原则。话语上,篡改对台湾问题的叙事,布林肯公开说“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学界炮制“和平统一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虚假叙事,一再突破中美关系“红线”。7月,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挑战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中的涉台内容。种种言行暴露出美方利用台湾问题“绑架”中国发展步伐的危险苗头。
三是举全盟之力合纵制华。美国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组织美国外交的主线,几乎全部重点都在动员其盟友和伙伴上,通过打造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联盟、以供应链产业链“去中国化”为导向的经贸科技联盟、以“民主”“人权”价值观为诉求的意识形态联盟,欲使中国成为一座安全、高科技和民主“孤岛”。价值理念上,美国为“小院高墙”“友岸外包”、“去风险”、供应链重组等“帮规”赋予安全内涵,并将之注入联盟战略中。地缘政治上,美国在菲律宾增设四个面向台海和南海的军事基地,推动日韩向着历史性和解迈步并拉拢其加入排华阵营,升级与印度防务关系以及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系列行动表明,美国以针对中国为目标,加快武装和割裂亚太地区,中美矛盾激化的风险仍大。
二、中美互动升温的动因
自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以来,中国顶住了美方的攻势,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带动中美互动底线逐渐清晰,交往方式更加稳定。拜登政府面临复杂、深刻的内外矛盾和挑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全面对抗,因而在思考长远之计。在中美关系阶段性稳定现象的背后,各方都在为应对下一轮中美博弈升级而布局,准备迎接更复杂的新情况。
(一)拜登政府调整对华策略
当前美国大战略辩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应当优先投入多少人力、财力、时间等资源用于对华竞争?“竞赢中国”是否应当优先于所有其他议题,例如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移民潮、中东热点等,还是说只是诸多议题中的一个?美国思想界对此没有共识,⑤政界也出现不同主张。⑥究其原因,在于美国没能准确衡量“中国威胁”的大小,也未厘清对华竞争战略的性质、目标、内容、边界等,⑦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引起国内外质疑和担忧。
从美国国内看,对华竞争反噬自身利益。以经贸科技领域为例,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促进芯片制造回流等举措扭曲了全球产业链生态,不仅导致美国技术部门巨大亏损,还对相关链条上的其他环节造成损害,它们实际上难以割舍庞大的中国市场。长此以往,最终可能是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降低。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英伟达、高通公司等芯片企业大力游说美国政府,敦促其重新考虑相关政策。⑧从国际看,美国的产业政策造成外交成本。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汽车业、半导体行业、绿色能源及技术受到美国相关政策的冲击,引发彼此竞争,但补贴竞赛可能会拖垮盟伴国家那些自身竞争力不足的产业。相关国家已对美表达不满,美方协调联盟的成本明显上升,不得不适度放松在对华政策上的张力。
(二)中国运筹中美关系的主动性上升
长期以来,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主动出招多,动辄下定义、提要求,中方被动做出反应。如今,中方展示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设置议题、管理议程、贡献方案、塑造合作等方面的愿望和能力都有所增强。例如,中方用“和平”为中美关系定性,把“不冲突、不对抗”作为发展中美关系的首要前提提出来,得到美方的共鸣。中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敢提要求,有坚持,能克制,灵活运用对美斗争与合作的“两手”,也是中方主动性上升的体现。
在同美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主动性需要有极大耐心。这种耐心不是被动等待,而是提升中国自身的实力,同时不放弃做美国各界工作,并按照既定外交方针,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面前,中国比美国的盟友有更大行动空间,不会用自我设限的方式去换取美国“保护”,而是有能力按计划推进自身的发展战略、国际经济合作、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外交军事战略等,并能够坚持使用对话和协商这种中国所青睐的打交道方式,引导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的持续发展壮大是中方运筹中美关系的能力基础。例如,今年1月至7月,中国实际利用美资金额同比增长了25.5%,⑨这有助于提升美企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国也根据美对华制裁情况,坚决予以反制。5月,中方以“网络安全隐患”为由,制裁美企“美光科技”。推动取消此项制裁便是美国参议院舒默代表团来华的主要诉求和议程。8月,中方宣布针对稀有金属镓和锗的出口进行管控。中国企业也迅速响应,减少对西方国家的稀有金属出口。经过中方的有力反击,美方已意识到推行对华对抗不可行,贩卖“新冷战”不可行,组建所谓“反华统一战线”不可行。
(三)“中间国家”对中美关系有制衡作用
中美以外的“中间国家”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消极走向有一定牵制,它们成为助推此轮中美互动升温的重要外部力量。例如,美国举办“民主峰会”,在国内外遭到冷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21世纪国际关系是“民主对抗专制”的叙事,此时美国若继续打“民主牌”,将不仅难以团结到人,还会凸显自身“民主乱象”的制度弊端,弱化自身影响力。再如,美国号召各国采取制裁俄罗斯的集体行动,却得不到“全球南方”的跟随,美国不得不从地缘政治意义上重新重视这个国家群体,听取它们对“西方主导的秩序”的不满,做出满足它们对发展议题的关切的样子。此外,大多数国家担忧美国对华竞争目标模糊、愿景危险,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欧洲蒙受对俄和对华制裁的经济损失,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上升;亚太地区国家试图平衡大国影响,选择走“复合型结盟”的“第三条道路”,⑩希望避免传统的两极模式,这在客观上对中美关系的消极走向形成牵制。
美方认识到,它与盟伴的对华政策存在显着温差,这导致它难以同时推进对华竞争战略和创新盟伴战略,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消除各方对“联盟制华”的抵触,使用对华竞争的另一面——即“管理竞争”来向外界表明,美方能够处理好对华关系。这么做的目的还是在于缓解外界担忧,拉拢国际人心,推进一致对华。
(四)全球性挑战呼唤大国合作
随着全球性危机日益频繁发生,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并非中美关系,而是如何解决严峻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尤为重要。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巴以冲突大规模升级、伊朗核协议陷入僵局、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美尤需合作应对变局。今年来,中国推进“三大倡议”,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斡旋沙特与伊朗和解,为巴以停火止战奔走等,践行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拜登政府作为民主党建制派主导的一届政府,也重视让美国重回国际合作议程,寻找发挥影响力的新抓手。
以往,全球性危机常常成为中美在全球治理诉求下推进战略合作的契机。例如,小布什时期,中美因反恐合作进入“建设性合作关系”,开展前所未有的功能性合作。奥巴马时期,中美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战略关系”。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经过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政策动员,对华“威胁认知”发生巨变,对华合作面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全球治理合作被置于对华竞争的框架之下,中美关系很难回到以战略性合作为主导的关系状态。
无论怎样,国际社会过去三年多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所经历的大国合作缺失、全球治理体系局部“塌方”等教训告诉我们,大国之间的合作也许是靠道德或制度约束来产生,但它根本上是各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应当是人类学习能力进化的产物,是国际政治向前演进的结晶,是让国际社会有序运行的常识和本能。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论或逻辑推理来证明。中美有责任通过双边合作来推动全球多边合作,这反过来也能扩大中美关系的空间和功能,约束中美关系的竞争面。
三
、前景展望
下半年来中美互动升温的态势表明,尽管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已定,但中美仍有共同利益,在近期找到了和平共处的方法,其理当进一步助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特别是要看到,当前中美关系氛围的改善有美国重新评估对华政策、调整战术、中国运筹中美关系主动性上升以及国际体系制衡等深层次和结构性因素,这决定了双边关系阶段性稳定的局面有可能在未来维持一段时期。
未来一段时期美方发展对华关系的框架可能包括:一面通过加码制裁、干涉内政、联盟制华的方式阻止中国崛起,另一面在对美国有利的领域展示合作姿态,避免走向对抗,确保经过长期竞争达到“竞赢”中国的目的。并且,合作的轨道已从属于“竞争”,合作的空间显着收窄,与其说是美方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不如说是美方面向它所希望争取的国际观众、盟友、伙伴的合作。对中方而言,要接受双方高层互动并不足以从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的现实。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从总统大选看,拜登已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现在将是2024年选战消耗掉他全部政治资本之前与中方互动的最后机会。当前互动取得的任何进展和成果,都可以成为拜登在选战中随意撕毁的“价签”,以展示对华强硬。当前,拜登政府基于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在气变方面寻求对华合作,但共和党与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若赢得2024年大选,很可能推翻中美气变对话的势头和成果。从国会选举看,国会两党议员一贯在对华政策上比狠斗硬,在大选中“谁也不能输”的心态更强烈,可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更大的破坏性作用。从外交看,鉴于美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很多国家可能会和中国一样,担忧与美国对话合作的可持续性,因为毕竟等到下一次选举,一切会从头再来。
注释:
①“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上网时间:2023年10月5日)
②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J. Blinken remarks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上网时间:2023年10月5日)
③参见王鸿刚:《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两手”与“新两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3年8月1日,转引自: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30814/42922.html.
④“Countering China: Advanc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and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 of Thea D. Rozman Kendl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Export Administration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Committee, May 31, 2023, https://www.banking.senate.gov/imo/media/doc/Kendler%20Testimony%205-31-23.pdf.(上网时间:2023年10月5日)
⑤Stephen M. Walt, “Here’s How Scared of China You Should Be,” Foreign Policy, August 7,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8/07/china-rise-geopolitics-great-power-scared/.(上网时间:2023年10月5日)
⑥Majda Ruge, “Primary concern: Trump, Ukraine, and the Republicans’ 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