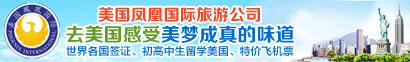鍾 倩
影視劇《紅高粱》熱播,好久沒有坐下來看劇的我竟成為追劇一族,被那片紅高粱地所深深吸引,好像是一種親切的引誘,觸及到心底最柔軟的部分。和朋友聊天說起,她也在追這部劇,徒生臭味相投的歡喜。她激動地說:「劇中提到任何一個高密的字眼,我都熱血沸騰。」原來,她是濰坊高密人。
網上對《紅高粱》的評價褒貶不一,不少原著粉兒覺得周迅飾演的九兒沒有鞏俐的潑辣和野性,整個劇也缺少鄉土味兒:單家大院被搬到城鎮上,給人深宅大院的熱鬧感,紅高粱地的荒涼感和空曠感一掃而光。朋友認為,「影視劇比影片更長更詳細,容易暴露出一些瑕疵,無需苛求完美。但是,畫面質量提高了,人物刻畫得生動了,追劇的人多了,這便是一種成功。」她的觀點我比較認同,「有爭議不是什麼壞事,觀看本身便是對經典著作的熱愛,也是鄉土情懷的流露。」那一片紅高粱地,是莫言的,同時也是我們的。
長大後,我們或背井離鄉打拚,擁有第二故鄉,或整日忙碌不停,產生冰冷隔閡,故鄉變成茫茫視線之外的小圓點,抑或停留在紙上的概念而已。一面是每個故鄉都在消失,內心的那份感情被連根拔起,一面是人們的迷失,走得太快靈魂落在後面,這些都是殊途同歸。然而,慶幸的是,我們還能在屏幕中找回一份慰藉,喚醒漸忘的記憶,尋覓最後的老根。
近日,我重讀蕭紅的《呼蘭河傳》,感受頗多。之所以想起閱讀,完全是一位作家提出的問題,他在演講中問道:「蕭紅離開家鄉後,為什麼再也沒有回去過?」我思考好久,覺得是她童年沒有得到母愛,而且父親不讓她上學、為她包辦婚姻,她心生恨意,逃離福昌號屯的家,逃出鄉坤家庭的樊籠,故鄉成為傷心地。轉而想想,若是沒有留戀,她何以寫出《呼蘭河傳》呢?閱讀的過程中,我的答案漸漸明晰。
蕭紅的童年,不都是荒涼的,「雖然父親的冷淡、繼母的惡言惡色,祖母用針刺我的事,都覺得算不了什麼,何況又有後花園呢?」後花園裡有祖父的愛,有儲藏室探幽不盡的神秘,有蜜蜂、蝴蝶、蜻蜓等的陪伴。她曾將玫瑰花插在祖父的頭上:「滿頭紅通通的花朵,祖母看見大笑起來,父親母親看見也笑了起來,而以我笑得最厲害,我在炕上打?滾笑。」此外,家中房客的生存狀態使她過早地感受到底層的命運。「那邊住?幾個漏粉的,那邊住?幾個養豬的,養豬的那廂房裡還住?一個拉磨的。」性情古怪的有二伯,生命頑強的馮歪嘴子,悲慘的小團圓媳婦,在蕭紅的筆下,流淌出綿密的悲憫和堅韌。比如,馮歪嘴子妻子死後,他堅強的養活兩個孩子,「他覺得在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
離開家鄉後,蕭紅的生活只有兩個字:流浪。1932年春,她回過呼蘭縣一次,商量和汪恩甲結婚後的經濟問題,因為沒有履行習俗的結婚手續,不為張家家風所容,所以沒有回家。多年後,她貧病交加之際,在哈爾濱街頭和父親相見,居然冷眼相對,形同陌人。從落難東興順旅館,向報社呼救求援邂逅蕭軍,到寄居裴馨園;從流落到歐羅巴旅館,到前往武漢,她飽嘗貧窮和飢餓,最困難時,一根鞋帶都要分成兩段,像她的詩所說:「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要酸。」唯一的撫慰是蕭軍的愛情,「我們常常用玩笑的、蔑視的、自我諷刺的態度來對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艱難,以至可能發生或已發生的危害。」邂逅魯迅先生,對她也是極大的鼓舞,魯迅的來信成為她和蕭軍的精神食糧。吃過午飯,他們沿?拉都路向南散步,用6枚小銅板買兩小包花生米,邊走邊讀魯迅的信。「兩顆漂泊的、已經近於僵硬了的靈魂,此刻被這意外的偉大的溫情,浸潤得難於自制的柔軟下來,幾乎竟成了嬰兒一般的靈魂。」
一路走來,蕭紅並沒有忘記故鄉,且是那麼的一往情深。她很少寫詩,在東京期間,寫過一首《異國》:「這窗外的樹聲/聽來好像家鄉田野上抖動?的高粱/但,這不是,這是異國了/踏踏的木屐聲音有時潮水一般了。//日裡,這青藍的天空/好像家鄉六月裡光芒的原野/但,這不是,這是異國了/這異國的蟬鳴好像更響了些。」1940年,蕭紅和端木蕻良來到香港,她重拾起筆,完成《呼蘭河傳》。之前居武漢時,她沒有大塊的時間專心寫作。「你這部長篇應取你家鄉的一條河做名字」,端木說道。她回答:「我家是呼蘭縣,縣裡有條河,叫呼蘭河。」「從你童年寫起,像呼蘭河水一樣涓涓流過,你跟?這涓涓流水成長,多美。」他說。
故鄉是一個人的私密處。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故鄉是無聲的哺育,最初的愛與希望、童年的快樂和傷痛,是烙在我們身上的戳印,不管走到哪裡,不管歲月如何洗刷,都如影相隨,永不褪色。蕭紅童年缺乏母愛,更多的是,男權文化的壓制,使她產生深深的牴觸情緒。家鄉的那個大水坑,只有男孩子才敢跳得,她勇敢地跳過去,從那時起,她的心已經翻牆而出,飛向自由的天地。短暫的一生,她顛沛流離,特立獨行,心底的恨和痛在潛滋暗長,每一次的隱隱作痛,都會掀起排山倒海的潮水,但是,她對那一片黑土地的眷戀,依然內斂地存在,只是被接踵而至的苦難、大片大片的悲涼所淹沒。
為什麼蕭紅再也沒回過故鄉?她的愛與恨成為一個綜合體,難以剝離,令她欲罷不能。最終,她將思戀和懷念都抒發在文字中,以這種外人不易覺察的方式,找到精神的歸宿。「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個女人」,說到底,她的不幸,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只有設身處地體悟到她的痛苦,才能讀懂她的選擇。影片《黃金時代》中有一句台詞,令我記憶深刻,「我不能選擇怎麼生、怎麼死,但我能決定怎麼愛,怎麼活,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黃金時代。」她尋找到屬於自己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曲折迂迴的過程中,她一次一次地回到呼蘭河,是在精神上。
「人不是光靠吃飯長大的,它也靠情感。情感在我們相互之間可以灌溉你,使你健康,使你成長,長命百歲吧!這一點千萬不要敷衍。」這種情感,正是鄉愁。很多時候,我們的離開,不過是暫時的流浪,終有某個時刻或某個時期,是要回去的,要麼葉落歸根,要麼精神回歸。像一位老者,一聽到秦腔,他便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秦腔喚醒了他心底的那個「情」字。
總有一種情感叫我們淚流滿面。無論莫言的紅高粱地,還是養育過蕭紅的黑土地,都是一種提醒:有些東西,失去了將再也找不回來,有些時候,失憶將會成為終身遺憾。「我要還家,我要轉回故鄉。我要在故鄉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聲談吐。」詩人海子的心聲,亦是我的真實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