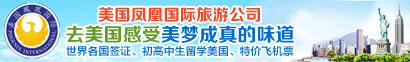蘇湘紅
母親過世之後,眼見日日形單影隻的父親,我一陣陣悲湧上心頭。
當父親說要到生我養我的村莊住一段時,我答應了。
一日,父親來電說,如今能動得手腳的年輕人都到廣東或江浙一帶的地方打工覓食去了,一天到晚,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我想買頭牛,每天浪浪牛,沒人說話時,跟牛說說話也好。
我知道父親想給我出血,但我手頭並不寬舒,我想到作家余華的那個名篇小說《活著》,裡面那個主人公悲情到最後只有跟一頭牛聊聊心情時,我妥協了,偷偷取出三更燈火五更雞熬夜寫出的豆腐塊得的丁點稿費,給父親買一頭父親寂寞時能給父親自言自語說話能給父親帶來歡樂的牛。
拿到錢,父親相面牛去了。
父親到鄰村去買牛的那個日子天氣好晴朗。
中午,一聲灑脫渾厚的牛哞聲劃破了村莊的寧靜。父親和牛頭頂麗日,一前一後在村口出現。村人全都走出屋,前呼後擁著黃牛。一群群看客,迎新娘一般熱熱鬧鬧。
牛挺精神,從蹄腿到身尾,從五官到牛紋路,在眾鄉親眼裡都無可挑剔。人們誇完了牛就誇父親,誇得比伯樂識千里馬還玄乎。
家添一頭牛,父親的事就更多了。農忙,沒有人手放牧,父親幹完地裡的農活後再貓著身子上山去割青草,天幽暗時才急急扛回家;農閒,只要天不下大雨,父親就堅持每天早晚各放牧一次。
每一次父親喂牛時,黃牛邊嚼邊昂頭望父親,不時發出一兩聲低沉的道謝,那是一種父子般親切的熱流交遞啊!
深秋翻耕,初春開播,牛蹄踩響了季節。這時,手撐著犁鏵的父親,嘴裡極富韻味地吆喝著牛,被犁開的泥浪,搖曳生姿,溫馨新鮮的泥味不知酣醉了父親多少個甜夢。父親趕這頭牛犁著自家的和鄰居家的責任地,肥沃與貧瘠,刻下了父親和牛的一片片辛勞。
擁有這頭牛是父親的榮耀。那些日子,牛販子紅娘踏破門檻,甚至途中攔截牧牛的父親要買這頭牛。父親未免預感有些不詳。一日,一牛販子把牛審了又審後,高揚起兩個手指:五千元。而父親就是緊緊抓住繩子不放。父親說,等過完我這輩子你再來開價吧。
事情總是讓人難以預料。
一個週末的下午,父親準備給牛添第三次草料的時候,回娘家看望父親的堂姐正在剁豬菜。突然,一陣沉鬱痛苦的呻吟聲從牛欄裡傳來。堂姐側耳傾聽,這不是牛哞嗎?急忙跑到牛欄,黃牛已直挺挺地躺倒了。堂姐大呼,不好了,牛中毒了!父親也急如流星般來到。
隨即,搶救在驚慌失措中進行。儘管父親灌了幾個臭雞蛋,牛哞聲還是漸趨微弱,最後什麼聲息都沒有了,牛欄裡彌漫一陣陣透心的冰涼。
事後聽老家的人說,事情來得非常的突然,前前後後不到半個小時。
父親當時象我母親過世一樣的哭了,兩行清淚順著他溝溝坎坎的臉龐流下。我的父親滴淚橫流的哭訴著:牛呀牛,你怎麼一聲不吭就走了啊……父親以一種大山裡的男人和一個一輩子跟泥土打交道的莊稼漢最悲傷的聲音哭訴著,淒涼的哭聲小錘一樣一叩一叩敲擊在每一位垂首默立的老家人心上。
黃昏,鄰居幾個叔伯按照慣例,心照不宣的來幫忙處理牛。
開膛時,父親呆坐在屋的一偶,不忍心瞅上一眼。
晚飯時,父親只喝了幾口悶酒,就酒醉一樣蹣跚離座了。
我四弟後來酒醉後跟我說,三哥呀,那晚我們的父親在15瓦的燈影裡的身影,就像磨房裡那只不會言語的石碾。
想起我恩愛了一輩子的父母如今已過世三年的母親和我現在形單影隻還在塵世裡奔波勞累的父親,我把頭埋到深深的膝蓋裡,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