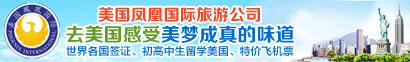春天徜徉在巴黎,你就会开始想象人间的乌托邦。要有一支妙笔才能形容这座城市春天里第一个晴朗的日子,因为前人已经描绘了不知多少次。就像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还有其他所有人在歌里唱过的:
... April in Paris, chestnuts in blossom
Holiday tables under the trees
April in Paris, this is a feeling
That no one can ever reprise
大意是:我看到漂亮的人们闲坐在精美的建筑下,在阳光下享用美食。这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极美景象。我要是再形容下去,恐怕会变成一首蹩脚的情诗。然而这里也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乌托邦是怎样逐渐创造出来的?好运只是一部分原因。法国人为了保护春天的巴黎,会做得很绝。
每个国家都有一两件事做得很出色。意大利人懂咖啡,日本人讲礼貌,美国人能跟陌生人聊天,德国人目不转睛地直面本国历史,英国人有缺点,但对自己的缺点很幽默。法国人懂得如何生活,春天的巴黎更是把这种擅长发挥到了极致。个中缘由想必值得深究。
想要有一个美好的春天,首先要有一个恶劣的冬天,巴黎就是如此。“当冷雨不停地下,扼杀了春天的时候,这就仿佛一个年轻人毫无道理地夭折了,”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他回忆巴黎的书中写道,这稍微有些夸张。因为巴黎的天空比伦敦更清澈,冬天也更凛冽,然而巴黎很少出现北方典型的白茫茫的冬天。即使湖面真的封冻,人们也只是待在室内,一边喝热巧克力,一边咕哝抱怨,而不是在冰上游弋亲近自然。
巴黎的冬天似乎没有尽头,然而巴黎却是为了阳光而建的。就像是一座地中海城市被轰隆一声扔到了北方:建筑物是白色和灰色,如此设计仿佛是为了让影子嬉戏,里面的公寓房间窄仄,使巴黎人想要从中逃离。
他们之所以需要逃离,部分是因为许多巴黎人曾经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农民。传统上巴黎人口来自于衰落的法国乡村。即使生在巴黎的家庭也经常声称,他们“其实”来自曾祖父离开的小村。我曾偶然读到过一部《麦格雷探长》的侦探故事,场景就设定在50年后我居住的巴黎的街道(你在巴黎做的每一件事都已经被人在书中描写过、在电影中拍摄过),乔治•西姆农(Georges Simenon)在其中描写的温暖夜晚里的街道将我打动。他写道,居民会把椅子放在人行道上,重新创造出已经失去的乡间户外生活。
伦敦的冬天和春天几乎无法区分,因为这两个季节都是阴云笼罩。而在巴黎,春光来临时就像有人打开了灯。咖啡馆外面出现了露天的咖啡座时,就好像居住的公寓面积一夜之间大了一倍。称赞露天咖啡座如果想有些新意,同样是难上加难。伍迪•艾伦(Woody Allen)对此会这样搞笑:“我在一家户外咖啡馆碰到一个人,是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奇怪的是,他还以为我是安德烈•马尔罗。”然而露天咖啡座的确把巴黎变成了一个舞台布景,人成为了布景。这也是椅子冲外摆放的原因,这样食客才能审视路人。
同时,路人也可以审视食客的盘中餐。春天的巴黎就像是法国美食的一场户外展览。这全都构成了法国乡村生活的假象,不过并没有乡村生活的单调,因为你正身处文明的中心。春天的第一天,我看完一部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电影,走路回家。
春天,有些巴黎人甚至会微笑。微笑在某些地方不值一提,比如在佛罗里达,人们即使刚被银行收回房产也能挤出笑容。但在巴黎,性情乖戾是社会认可的模式,微笑就显得令人震惊,就好像有人刚刚在酒里放了些LSD(一种致幻剂)。
简而言之,春天的巴黎是一件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然而她十分脆弱。乌托邦很容易被打碎。例如,意大利人本来创造出了观赏足球的完美体验,但又用破旧的球场、足球流氓和假球黑哨破坏了这种体验。布鲁塞尔据说曾经和巴黎几乎一样美好,但战后城市规划师把她毁了。
法国执政者每天都在处心积虑保护巴黎。他们不只是把所有平凡的事物,比如政府大楼之类,铲到巴黎环路之外的荒芜之中。1940年6月,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意识到法国人会做到什么地步。当时德军已经攻入法国,丘吉尔飞往法国,他自然而然地料想,巴黎会有一战。他问法国人:“巴黎群众和居民难道不会迎战,分割、牵制敌军吗?”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不以为然:“把巴黎变成废墟也不改变问题。”法国将军魏刚(Weygand)补充说,“(在巴黎)不会有人尝试抵抗……不能见到巴黎毁于德国轰炸。”
这也是今天我们(付出代价后)在巴黎仍能享受春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