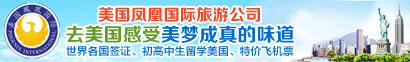恋爱其实并不苦恼,但也不是那样放纵地欢乐,仿佛一种宁静,走进很深很深的心里,让你有了一片可以歇息的美荫……
{1}刻骨相思自不磨
相思你苦楝你合欢你凤凰妯学校里的四种树木妯前人说那是爱情的四个阶段妯是大学的必修学分。
说实在妯我不太懂妯图书馆后面就是一片茂密的相思树林妯但我不曾走进去。我只喜欢起风的时候妯在图书馆的廊下妯倚着石柱翻开杨牧的散文孟“又是起风的时候了妯许是这小岛接近大陆妯秋来的时候妯秋便来了。季节的递转那□真确那□明显。”抬首望向无痕的蓝天妯西风摇曳图书馆前的老榕树妯那样蓊郁那样生姿妯于是便好象懂了一点秋天妯懂了一点杨牧妯懂了一点文学……不然便是一整夜与同学在烟雾袅袅的斗室妯很正经地争辩一首诗或一篇小说妯或就着醉意妯朗读“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妯对着一壶苦茶妯我设法去理解……”黎明的时候漫步在薄雾与满园的鸟鸣声中妯亲切地嗅到樟木迟缓而古老的清芬妯对从小生长在都市的我而言妯此刻好象才明白了所谓大地的芬芳是怎□回事。或者妯在寂寥的课堂上,揣摩着“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苦”的意象,但那些绣金织银的翠鸟,熏香浓妆的红泪,怎□说都是太过古典的爱情,难学亦难工。
在女生宿舍的红墙绿柳外,接近石屋小邮局的路旁有棵菩提树,那是我们相约的地方。立在一棵大树下等待女友,无论夹着一本书或拄着一柄伞,大约都带着一些呆气,所幸菩提树也不是那种迎风生态、袅娜多姿的潇洒树种,一人一树,悠然却也满怀心事,仿佛有那□一点点相思的味道。
我们相约一起去吃早餐,穿过学校密林筛下的淡淡晨曦,“我梦里的蓝袈裟,已挂起在墙外高大的旅人木”,我并没有看过蓝袈裟,也没见过什□旅人木,但我喜欢那□光明磊落但也隐含寂寞的描写。我告诉她这首小诗,她平静地微笑,也不说好或不好。并肩穿过牧场的晨光,云淡风清,牛儿在远处嚼草,恋爱其实并不苦恼,但也不是那样放纵地欢乐,仿佛一种宁静,走进很深很深的心里,让你有了一片可以歇息的美荫。
多年后,我们在学校的小教堂结婚时凤凰花正开得艳红,菩提树对面的钟塔上敲响清越的晓钟,剎那间大一时初闻这钟响时的感动又涌上心头。那时朦胧地知道人间有一些难忘的神圣与美好,却不知是在何方,又与自己何干?而此刻已是那□临近,那□真切。我突然想告诉新娘:相思、苦楝、合欢、凤凰是学校里的四种树木,前人说那是爱情的四个阶段,是大学的必修学分。但我一直没讲,我猜她大约是平静地微笑,也不说好或不好。
{2}望尽天涯路
多年不见的学生写e-mail告诉我,那棵树还生长得很好。几年前我在台湾中部一所偏山上的C大兼课,C大绝世而独立,学生老师人数不多,都像修行人。那时基业初肇,土木方兴,尺长腕粗的蟒蛇偶尔出没,校园里几栋新建筑隐隐透露出开山立派的理想与豪情,树木花草,也分不清是人工还是天然。从教室到餐厅,中间是一片好大的草场,被同学走出一条隐约的土路,放眼望去,只有一株伶俜的瘦树兀立,不知是偶然被留下的,还是刻意种植的。据闻那片草场是文学院预定地,只是经费一直拨不下来。
我那时还未毕业,一路转车颠颠簸簸来到C大,除了上课,不知为何特别关心那棵孤树,总觉得它那样藐小单薄的身影,却有着极坚毅的神情。冬天时它枝叶全雕,春天时却又沾满新绿,似乎为我前途茫茫又遭逢家变的人生,提示了生命的真相,在许多颠沛的旅程中,闭上眼睛便想起这位会心的良友,经常让我顿觉开朗。
数年后我就要离开C大了,文学院的预定地还是只有那棵孤树。我对学生说,那棵树便是文学院的象征,代表文学的纯洁以及无私无欲的生命。也许等学院落成,可以将它移到中庭,听听古典与现代的雄辩;倘若真要被砍伐了,大家也应该为它系上黄丝带,并举办一个晚会,轮流念诗到天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重回C大看看,也不知文学院是否已然竣工,但对于文学,我还是喜爱其纯洁与无私,仍热中于追想与尝试。只是生命里少了那八千里路的云和月,相对而言是迟钝了,是耽溺了。当时一味恼孤桐,回首阑珊筵已散。回首青春的行旅,春树暮云是飘泊和相思,我也不禁感到岁月,感到寂寞了。
{3}换得东家种树书
为竹浇水,为花施肥,手栽薄荷茂而不葺,荼蘼含英且未开,小小窗台也得这样绿意,这片闲情。
几盆花花草草,小小的发财树最能讨喜。它连根至顶无过三十公分,很难满足我对树的定义与想象,不过细观其干其柯其叶,倒真是一棵具体而微的小树,也许它是上帝依照一○○:一的比例,所小心造出来的模型树。记得有首题为〈现实〉的新诗:“我的委屈着实大了:因为我老是梦见直立起来,如一参天的古木”,面对植在小小瓷钵里的发财树,我对它有些抱歉,亦有一些期待。
不过我却愈觉这株小树的可爱,“发财”这俗土的名字,实在很适合我当下的心境,虽然我从不买彩券,也不作什么投资,但是能有一笔意外的收入(如在床底下发现一只聚宝盆),让我添一套音响数张唱片,或是购置几座大书橱也是很好的。有志文学而贪恋钱财者文格必卑必弱,最是不可取。不过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非常计较钱财,早年以为那是一种辱词,近来渐渐觉得那也许包含了一丝肯定(虽然还不至于赞美),要能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没有一点守财的性格是很难办到的,尤其在台湾当前这个如狼似虎的社会。因此当初在阳明山的花圃,得知这美丽的小树有着如此有趣的名字,便决定将之恭迎回家,日日作一个发财梦。
人生里总有太多的志业等待完成,但大多数人最后所能完成的,只是事业而已。我也曾有许多如此如彼的幻想,但近来像阖上一本又一本的书册,我关上了那些淑世抑或奉献的想法,被逼在一条生活的轨迹里周转,卖剑买犊,归去来兮。这样的心性不免爱读范石湖与辛弃疾晚期,也不免更容易被某些江山泣血的文字感动,但也更容易遗忘;最不免的是开始关心养生与留意玩物丧志的那一套东西,像个不再革命的退党党员,慢慢布尔乔亚。
“现实”实在是一个极妙的东西,有人被它逼得作了英雄,有人因为它而零落同草莽。我每天为小小的发财树浇水,乐见它在严冬里,依旧葱笼昂扬,也盼其终有一日成为参天巨木。人生的众芳虽然芜秽,但我也并不委屈,因为“现实”虽能让人安静地承认自己,守分地度过此生,然“现实”并不能阻止成长,也不能要求任何一株柔弱的植物,放弃怀抱幽贞的岁寒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