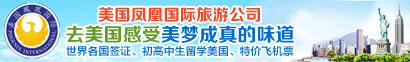汪兴旺
犁是古老的翻耕农具,主要由犁辕、犁铧、犁底、犁壁和犁梢等构成。
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装犁制耙,父亲好不容易瞅中一株弯脖子槐树,请来老木匠,老木匠因势就弯,加工成犁辕和牛轭,装成一张犁。犁厚实、笨重,足有几十斤重,对于“六十岁学吹打”的父亲来说,面临的是力量加技术的考验。
日复一日的耕作,父亲很快学会了犁田。这张厚重的木犁彷佛成了我家的一员,父亲熟悉并喜欢上它。后来,铁匠铺有卖铁犁,有人劝父亲换张铁犁,父亲却嫌铁犁单薄、飘轻,他说,还是木犁中用,虽说沉点,走犁稳,起土深,不留“黄鳝埂子”。
春耕开始了,犁每天由主人背着跟牛一道,去翻耕花草田。一路上,它欣赏到春天的画卷:燕子们轻快地掠过柳梢,红花草铺满田野;蜜蜂嘤嘤嗡嗡,小溪流放声欢唱……一冬的寂寞烟消云散。主人把牛轭头驾在牛肩上,一头由铁鍊子栓在犁的磨盘上,扶正犁稍,一声吆喝:“特叱——”牛拉动犁,泥土亲吻着犁铧,哗啦啦泥浪翻滚,田野裡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八哥们飞前飞后地捉虫子,凑热闹似地落在牛背上。犁不知不觉融入春耕的图画中。
犁最理解主人和牛的辛苦。“双抢”战斗打响了,抢收抢插,耕田任务紧,父亲天不亮就背犁赶牛下田,往往星夜才回。日头晒得牛背淌油,晒得田水滚烫,犁走的正正的,牛却开了小差,不走道儿,犁慌了神,步子七歪八拐,父亲也跟着一个趔趄。有时,牛“扑通”倒在水田裡,打起了泥笼,犁差点栽了个跟头。父亲恼了,扬起牛鞭,啪啪几声脆响,牛从泥水裡不情愿地爬起,摇头甩尾,好像报复似的,甩得犁一身泥水,弄得父亲睁不开眼。犁知道牛脾气犯了,默默地等候着,直到主人和牛都心平气和。
暮色降临,人困、牛乏,犁也累了,父亲把牛牵到塘裡,让牛洗个痛快澡,洗去身上干泥巴。尔后,将犁也扛到水边,卸下犁铧,擦洗乾淨,才带它们一道回家。父亲喂饱牛,把牛牵进栏裡,又把犁放进柴房,这才进屋洗澡吃饭。
夜深了,屋裡传来主人如雷的鼾声,牛栏那边也传来牛粗犷的鼻息声。月光泻进柴房的窗户,映得犁铧亮晃晃的,弥漫着一种清远的古意,此时,犁彷佛厚道的长者,显得平静而安详。
后来,村子的牛被卖了,没了牛,犁也不中用了。父亲的犁久久呆在柴房裡,它开始想念芳香的田野,想念昔日的耕牛,想念曾经背它下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