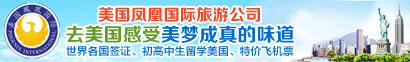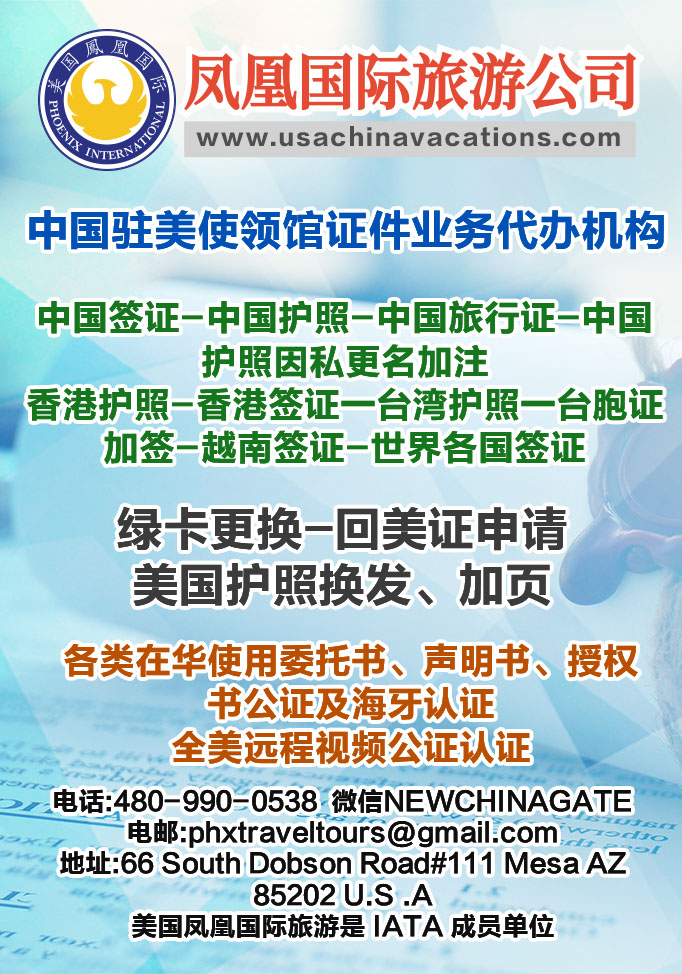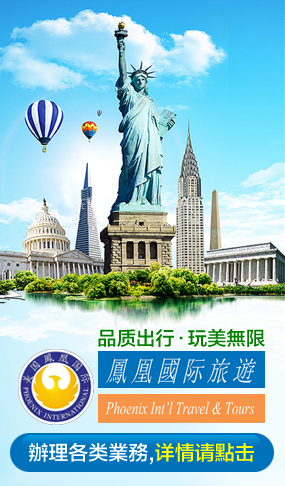潘愛婭
“稻籮被踢得滴溜溜的轉”,聽起來很好玩有趣的這句話,其實並不是在玩什麼有樂趣的遊戲。只有經過了那個特殊的年代,生活過那特殊的日子的人,才解其中的味。那不是趣味,是一種恥辱和心酸的味。
“稻籮”顧名思義就知道是一種裝稻穀的籮筐,竹篾製成,有大中小之分,是一種工具,也是量器,兩隻稻蘿就是一擔。以前的老年人,都是以多少擔稻穀來形容收成的。
在改革開放以前,還沒分田到戶時,農村是個大集體,以生產隊為一個小單位。按現在的語言來形容的話,生產隊裡也有著“留守”的兒童和婦女。
他們的丈夫或父親在外地工作,拿著國家的工資,婦女和孩子在農村生活。農村需要的是勞動力,而這些婦女兒童們,往往都是軟腳蟹子,是城市不要,農村嫌棄的,又幹不了重活的一批人。
農民們種出來的糧食,交完公糧後,才能分配自己的口糧。那年代又都是按人頭分配。而這些留守的家屬們,也是要吃飯的。幹不了重活,沒有多少“工分”,當然也就享受不了公平的分配待遇,只有拿出“錢”來稱口糧。
那些在外地拿工資的公家人,其實也拿不了幾個鈔,每月高工資的也不過三四十元。要拿出很多錢來買口糧,養活一大家子也也是非常困難的。
有時只好欠點錢,腆著臉去生產隊賒點口糧。在這時,農民的優越性被充分的展現了出來。看得出在那排隊稱糧食的隊伍裡,低著頭誠恐誠惶的人,肯定都是被“留守”的婦女兒童們。
“沒錢來稱什麼糧?過去”。鄙夷的聲音剛落下,稻籮已飛到老遠,並被踢得“滴溜溜”的轉。掌管大稱稈子的人,在這時是絕對的權威。
可憐的婦女孩子們,不僅僅是傷心,更多的恐怕是羞憤了,大家只得默默的靠到一邊去,大膽的人還想說幾句求情的話,愛面子人的淚只得往肚裡流。
要吃飯,要生存,只得撿起稻籮來,再次去排隊,說些好話,求這些生產隊裡的掌權人, 能開恩稱一點口糧,鄉里鄉親的,有那心腸軟的,也會通融一點的。要是遇到鐵面無私的人,那麼,稻蘿還會被踢得“滴溜溜”的轉的。像這種稻籮被踢飛了的現象,農村裡普遍的都差不多。
在那些歲月裡,鄉下人的鹽錢和花銷,只有靠母雞下蛋來解決,人的口糧都不多,母雞也就不會多的。所以,生產隊裡的經濟來源,也只有靠這些在外地拿工資的人的買糧錢。於是,矛盾也就存在了。
這一切,都成了現在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的往事。跟過去相比,現在的農村裡,已是家家小洋樓,豐衣足食。
“稻蘿”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被逐漸的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取待它們的是塑膠編織袋。而那種讓“稻蘿”排隊稱口糧的日子,更只是成為了閒聊中的資料了。
往日的“稻蘿”, 在人們心中留下的那淡淡憂傷,也成了永遠都抹不去的陰影。有過這種經歷的人,談起來還會很神傷。
不堪回首的過去,成了永遠的過去。現在的人們啊!應該好好珍惜現在的幸福日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