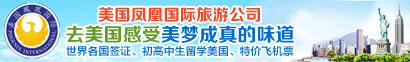从老民居的窗户,往外看见崭新的上海,这是上海人体面生活的一部分。图/图虫创意
“网红上海”不low,它又和之前的“魔都”“海派”一样,只是特殊时间与空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共同作用效果,是上海市民在某一时代与大环境下追求最优质生活方式的途径罢了。
谁也没想到,一个垃圾分类,就揭去了上海人的体面。
向来,上海人是摩登、精明、能干的。
他们可以浑身上下精致得不露一丝破绽,哪怕自家的破袜子其实并不舍得扔。他们的下颌骨似乎常常30度上扬,那也是因为上海确有令人自负的资本。
胡歌,上海人。
可扔垃圾的时候,上海人却是疯狂、窘迫的。
传说有人动用了无人机把垃圾抛向隔壁小区;传说有人每天还未清醒就要面对阿姨的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传说蟑螂屋里的蟑螂、科罗娜里的柠檬,都要抠出来,分开处理;传说上海人就要被垃圾分类折磨疯了,就像当年的网红流浪汉沈巍一样……
上海的垃圾分类开始了。图/图虫创意
都市传说几成为真,几成为梗,大都难以分辨。但这些麻烦的,带着垃圾的脏与臭的事儿,都集中发生在与其形象并不相符的上海人身边。这无异于揭发立志减肥的人吃了两碗大米饭,正人君子结果是女装大佬,大都只是戏剧效果。
看戏的人更愿意往其中添点油加点醋,将故事变成谈资,把上海人愈加地“疯狂”化与“妖魔”化。谁叫人的家就叫“魔都”呢?
一条黄浦江,划开魔幻的浦东与浦西。图/图虫创意
如今说起沈巍与他的流浪传说,大伙儿都要反应个几秒,翻翻看过的公众号爆款,才能完全回忆起这么个人。想必上海垃圾分类也不会让大家笑太长时间。
不久后,我们大部分人都要为自己门前的垃圾分类而苦恼。到时候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一边捡着自己手上的垃圾,还不忘扭头看看上海人分类做得怎么样了。
上海有一百种“上热搜”的方式,垃圾分类只是其中的一种。
它就像是一位有流量,有实力的明星;有无数粉丝奔赴,带着一点憧憬,一点迷惘;也有无数黑粉吐槽,带着一点嫉妒,一点不甘。
至于上海人本身,他们早已习惯自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话题榜的占有。这种习惯,这般气定神闲,本身就是一种体面。
十里洋场,上海的欲望之源
带我回上海回到我心之所向犹记彤光满路华灯初上夜空有钻石闪耀我合起眼就在这里与你相望不过片刻黄粱梦醒满目昏盲
《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年上映,导演程耳专门请BGM大师梅林茂为电影创作了《Take Me To Shanghai》一首插曲。
歌词、唱腔,搭配故事中的几段“罗曼史”,此片无疑指向了那个时代上海的关键词——欲望。
观众许久之前看到如此畅快的爱恨情愁,还是许文强与冯程程的上海滩。只是那时的欲望随着浪奔、浪流,要来得豪迈许多。
1849年,上海法租界建立,为资本主义与外国文化的渗入,搭建起了一个缺口。
《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一书记录了上海从这个时期到现代社会的整段历史。来自美英两国的作者这样概括上海:
上海,是一个充满了美妙的矛盾与奇异反差的国际大都会。她俗艳,然而美丽;虚荣,但又高雅。上海是一幅宽广壮阔、斑驳陆离的画卷,中国与外国的礼仪和道德相互碰撞,东西方的最好与最坏在这里交融。
福州路老照片
在东西方文化与特殊政策的交互作用下,到了20世纪初,上海便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处处皆是机遇,处处皆有欲望。
“一只破箱进上海,满船财宝返故乡”,是当时传播效果最好的一句广告。
除此之外,这里也为因政治原因南下的作家、文人、学者们,提供了一派自由的天地。据统计,1902年-1916年中国新创文学期刊达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上海独占其中22种。而当时的北京一家小说杂志都没有。
普通人在赚钱生活之余,也同样渴望娱乐、文学、戏曲与电影。在众多讲述老上海故事的文学作品中,乘坐黄包车前往大世界、新世界是最为常见的场景。
大世界宣传画
最近,上海海派艺术馆开幕,第一个展览的项目便是丰子恺的作品。丰子恺在上海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其中“被黄包车与热毛巾支配的噩梦”给他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他在《旧上海》一文中写,黄包车夫是最苦的,略犯交规,就要吃路警殴打。这些由印度人、越南人担任的路警,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也就是踢一脚,打一耳光。
外国人喝多了在路上横冲直撞,最惨的受害者也是黄包车夫,因为他们负担最重,不易躲避。
丰子恺亲眼目睹过黄包车夫被撞杀,从此不敢在租界乘黄包车。
吴宇森《天堂口》拍摄花絮中的黄包车。 图/新浪娱乐
热毛巾噩梦则发生在大世界。丰子恺回忆,
里面到处都是拴着白围裙的人,手托一个大盘子,盘子上放许多绞紧的热手巾,逢人就送一个,硬要他揩,揩过之后,收他一个铜板。他又亲眼目睹有人为了将这一铜钱用出性价比来,先“擤一下鼻涕,然后揩面孔,揩项颈,揩上身,然后挖开裤带来揩腰部,恨不得连屁股也揩到”。
这些毛巾当然会回收利用了,每成功“赠出”一次,上面仿佛就叠加多一层“复合维生素”。
丰子恺又从此不敢再进游戏场了。
大世界哈哈镜,上世纪60年代老照片
但他对大世界等游戏场的评价又不尽是负面的,因为这里“出两角钱买一张门票,就可从正午玩到夜半”。
他写上世纪初的大世界,一进门就是哈哈镜,照得人像丝瓜,像螃蟹,“没有一人不哈哈大笑”。而进到里面,花样更为繁多:各地戏剧场、放电影的、变戏法的、坐飞船的、吃饭的,甚至还有屋顶花园。
对比丰子恺的幽默吐槽,白先勇对上海的记忆则要美好许多。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也提到了大世界的哈哈镜,大光明电影院等地方,
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尽管白先勇也就是小时候在上海待了两年,但或许是有了童年滤镜加成,上海也成为了他意识形态上的家。
白先勇的“金大班”亦来自于上海百乐门。
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也在上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常与田汉、郭沫若、郁达夫、京剧演员黄玉麟等人来往。
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生动描绘了上海的生活细节,包括类似于“因为上海太过繁华,街道太过拥挤,以至于在街上走着,会不小心被黄包车的车杆戳到腰”的经历。
村松梢风写下,“来过上海的人往往将其称之为魔都”。“魔都”一词由此沿用至今。
海派文化,上海的化骨绵绵掌
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开埠以后来自西方欧美地区的各国文化,汇集在上海,并在这里逐渐形成一种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海派。
海派文化于19世纪末的上海孵化,在京派的正统文化看来,那抹遥远的繁华都是假象,是离经叛道。
左宗棠称海上画派为“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沈从文等人亦将其定义为“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
2013年6月6日,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海派旗袍日”在东方明珠塔盛装举行,上演了“千人旗袍地标秀”的景观。图/图虫创意
自从海派文化出现,“京海之争”便没有消停过。鲁迅是这场争论中少有的看得极开、极远之人。
他认为吹也是广告,黑也是广告,所以无论是“京黑海”,抑或是“海黑京”,那都是“一道暗送的秋波”,正好印证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
所以,“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新周刊》也曾尝试《换一个角度看上海》,发现“海派文化时兴了,上海人并不声张。海派文化的精髓就是阴柔与包容,化解一切坚固之器为我所用”。
梅兰芳先生在上海思南路87号的故居中度过了27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和艺术上最辉煌的成就都发生在那个阶段,其中包括他广为人知的“蓄须明志”。陈凯歌的《梅兰芳》在上海完成了大部分的拍摄。
鲁迅先生超前地领悟了营销、公关学的奥秘,而正如他所说,因为这一场“互吹(黑)”,海派文化得以在20世纪40年代,从非主流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流。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得到上海来露个脸,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喜爱。
这时候的代表人物?张爱玲。
向来以刻薄著称的张爱玲并不吝啬自己对上海的喜爱。她去美国之后也常常想家,
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 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1943年8月《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爱玲的《到底是上海人》。文章总结“到底上海人是什么样的”: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上海人的许多“不甚健康”与“智慧”都体现在了海派文学作品中。
《上海往事》海报,刘若英饰张爱玲,赵文瑄饰胡兰成。
比如他们的物质崇拜,就藏匿在小说刻意突兀的描写里。
像葛微龙看见,梁太太的别墅构造类似摩登的电影院,可屋顶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处处充满着不和谐。
像大小姐们走出弄堂,没转几个弯,就会来到朱古力糖果铺、拉萨曼烟店、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等地方。
后来的创作者再将海派文化进行理解并消化,由此诞生了亦舒和席绢来来回回的港台大小姐与小少爷的故事;诞生了郭敬明的《小时代》;诞生了“曼哈屯”等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是海派文化的“遗风”。
但也有人像海派文学那样专注描绘小老百姓生活,将之与意识流融会贯通,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景。这个人是刘以鬯,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创作事迹是写了《花样年华》的原著《对倒》。
精致的原著,出了精致的电影。
比如他们颇严重的自我身份认同感。海派文学还有一个永恒的主题,“乡下人进城”。《半生缘》世钧在上海人叔惠面前,就说“南京是个小城”。
再比如他们总是“坏坏的”,在算计些什么。
于是塑造了许多坏上海人形象的张爱玲不紧不慢地为自己与上海人开脱: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看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上海男人女人都不相信童话。
网红成风,上海精致的新衣
1933年2月17日,英国人萧伯纳乘皇后号抵达上海,蔡元培、鲁迅等人陪他逛了一趟世界社礼堂。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欢迎会在这里举行。
会后,萧伯纳漫步福开森路,称赞道:走进这里,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人想画画,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
这条美丽的福开森路,就是后来的武康路。
武康大楼,也叫诺曼底公寓。图/图虫创意
2001年11月20日,上海向全世界宣布,将投资180亿元,将南京路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商业街,对标美国曼哈顿、法国香榭丽舍、日本银座。
当时麦肯锡咨询公司给出的6点必要建议是:
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街区配备多重功能、支柱商业有更新力、基础设施与环境良好、街区发展两性管理。如今这些成为无数名人故居的街道,被按原样保护,有条文规定上海的46条马路不得拓宽。
南京路 图/图虫创意
当年的大世界又重新开张,哈哈镜还在那。顶楼的马戏团也和白先勇一般回忆起《上海童年》,里面的内容还有“秋风起,生姜拌好醋,用蟹脚蘸蘸伊”,还有大光明电影院和红房子西餐厅。
上海似乎一切都没怎么变,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几乎是全中国变化发生最大的城市。
创作了《繁花》的作家金宇澄说《股疯》是他心中最上海的电影。顾名思义,影片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老百姓跳入股市后的疯狂。操着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苏州话、苏北话、广东话、英语的人生活在同一片空间之下,和谐又充满骚动。
在这部1994年电影的最后,在股市里尝试过失意的人又带着客人看起了房产,说以后房地产定大有作为,说罢一手指向浦东那块地儿。
《股疯》片尾
进入21世纪,上海的收入、房价,都达到了绝对的高标准。
老上海牌的手表、眼镜和单车已经从历史舞台上谢幕,成为大家怀念但并不稀罕的物件,但人们还是为上海的平台与氛围所吸引。
曾经诞生过中国最顶尖思维、最优美文字的地方,经颇有名气的现代设计师改造,为“带着满身家当”进入上海闯世界的人提供了容身之所,也为网红们提供了排队拍照的去处。
上海人酷爱排队,这可以说是疯狂,也可以说是秩序。图/图虫创意
日夜流连在浦西的青年人是新旧媒体人都爱的采访对象,因为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只有诗,且不必去远方。
外国品牌、艺术项目进入中国,仍会首先来上海试试水,因为这里生活着整个国家最愿意为文化掏钱的人。上海电影节一开票,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便迫不及待不远千里地赶来。
派对成为了上海人新的交流方式,这里有世博趴、F1趴、维密趴。
清末企业家荣宗敬的荣宅,被改装成了文化艺术空间,成功牵手时尚大牌。
荣宅局部
而数学家徐光启葬在了徐家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后代子孙依然精通计算。余秋雨感慨上海人的“智慧构成了一种生命力,时时需要发泄,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
这些智慧如果发泄在徐家汇、陆家嘴这些地方,那便构成了中国的金融中心;如果发泄在芝麻绿豆的琐屑小事上,那只能是研究研究“今天卖小白菜的有没有送吾两根葱”,“跟侬相亲阿宁收入户口匹配不匹配”的问题了。
从小在弄堂里长大的小姐们当了妈,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去学钢琴和画画。学习不拔尖没关系,英语不要太洋泾浜的就行。
上海弄堂 图/图虫创意
而对海派文化有更多人生体验的老人们,有了钱,有了闲,泡咖啡馆、跳舞的好习惯是一辈子都甩不掉了。
他们常去的“老克勒”餐厅也是由老人来担任服务员,不过于谄媚,也不会失了礼节。据说,当年张国荣等港星就十分偏爱这种“海派”的服务模式。
上海人不断书写着“精致”“体面”在这片土地上的意义,一如他们当年定义过“魔都”“海派”一样。
到了21世纪,这些形容词,都可以用“网红”来概括了。
“网红上海”不low,它又和之前的“魔都”“海派”一样,只是特殊时间与空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共同作用效果,是上海市民在某一时代与大环境下追求最优质生活方式的途径罢了。
上海石库门老宅 图/图虫创意
这个过程中,他人的赞誉与非议,红与黑红,上海人始终不屑于解释。他们兴许正一手拎着干垃圾,一手拎着湿垃圾;依照鲁迅先生的逻辑,他们心里还会想着大家为上海做的“广告”,真是谢谢侬。
你瞧,法国梧桐的误会解除了,大家不还是叫它法国梧桐么?
参考资料:《制造“上海人”:都市共同体主体意识的苏醒》,何顺民《海派文学的隔空比照》,吴玉杰、李昊《论海派文学的传统》,陈思和《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王明洁《京派和海派》,鲁迅《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旧上海》,丰子恺《上海人》,余秋雨
✎作者 | 门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