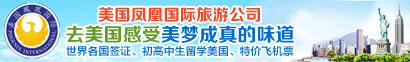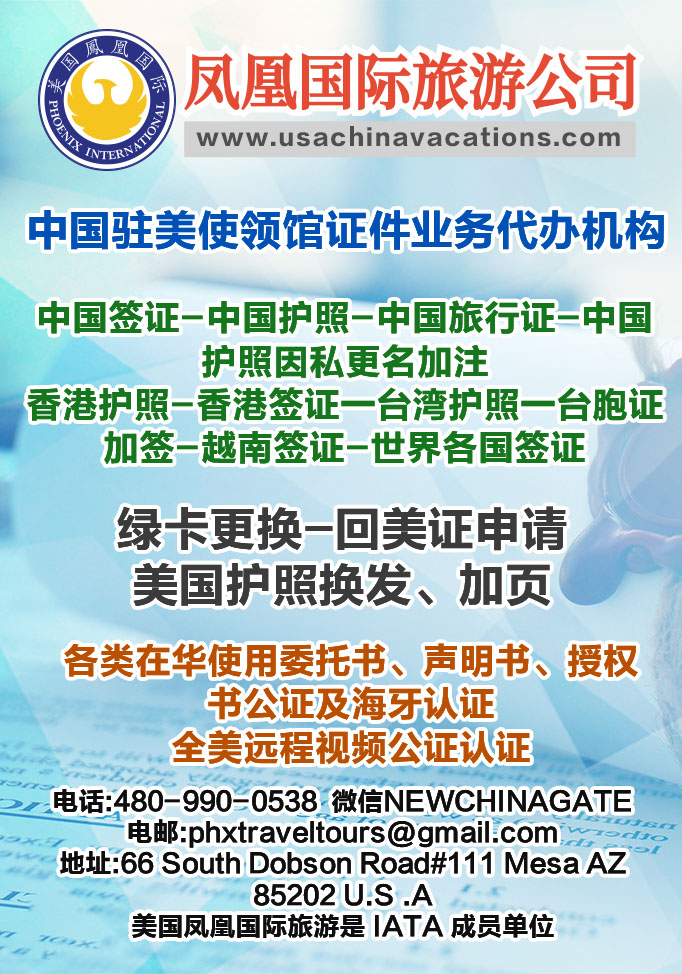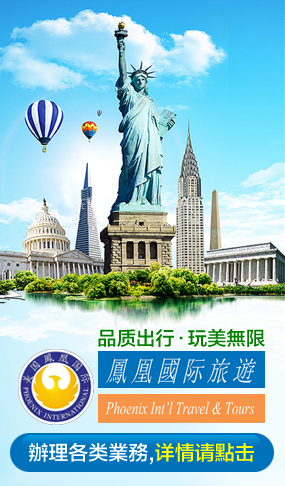□王太广
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面对别具特色的各种灯饰,会让我想起儿时的煤油灯。
我的童年是伴着煤油灯度过的。那时的灯,其实是用一只大口玻璃瓶盛一些煤油,找一块薄铁皮卷成筒,用棉线拧成一根灯芯,然后在大铜钱或者铁皮上钻个孔,把灯芯放在瓶口上。这样,一盏灯就做成了。
天黑的时候,我才开始点灯。点灯也有学问,必须用一根火柴就得把灯点着。点着后还不能让风把灯吹灭了,如果看到有人开门、掀布帘子或者走动,要赶紧用手把灯捂住。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火柴的消耗。二分钱一盒的火柴,在今天看来,实在有点不值得如此紧张,但那时,火柴却是紧缺物资。
省油的诀窍在于灯芯。要时常用剪子剪灯芯,将大火苗调整为“豆状”小火苗。在这微弱的火光中,什么都显得影影绰绰。
煤油灯往往是冬天点得多,夏天点得少。春、夏、秋的晚上,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月光下戏耍。等到玩累了,母亲就把我叫回家,借着月光铺褥子、放枕头,安顿我进入梦乡。冬天的晚上,我常早早地躺在被窝里,看母亲在煤油灯下纺线。她一边摇着纺线车,一边给我讲老掉牙的狼外婆和憨女婿的故事。我不是被狼外婆吓得心里发毛,就是被憨女婿逗得咯咯直笑。
我十四五岁时上了初中。初中有早晚自习课,我们上自习课时,都是端着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在教室里,我的一个煤油灯能让前面的两个同学和我的同桌都享受到光明。如果离灯近了,头发就会被烧焦。用了一晚上煤油灯后,第二天早上,每个同学的鼻涕都是黑糊糊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村里架了电线,装了电灯,开关绳一拉,满屋亮堂堂的。但这时的电力很不充足,停电是家常便饭,有电倒成了稀罕事。人们形容此时的电是“照屁股电”,意思是等人睡觉了才找来电。因而,家家户户还是少不了煤油灯。
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进行了电网改造,电灯才真正成为农民的照明工具。如果不是线路检修或者特殊故障,全天24小时电力充足,停电则成了稀罕事。
故乡的煤油灯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和艰辛,学会了节俭和忍耐。每当我在日光灯下读书写字的时候,我总会告诫自己不要忘记与煤油灯相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