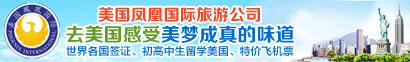星期一的早上,全家人都睡过头,照例十分紧张,偏偏越紧张越要出故障:先是大黑临走前发现装乘车卡的钱包找不到了,我们说了他两句,他黑着脸离开家,把门摔得差点蹦出门框;然后我跟二黑一起出门,这个粗心大意的孩子,一下子忘记这个,一下子忘记那个,开门关门地折腾了两三趟,好不容易上了车,照例开到学校附近的街上,该他下车自己走去学校,我好继续往前开去公司,但是他又说太晚了,怕进不去大门,要我一直送他到学校门口。我不答应,他就哭着说不去上学,要自己走回家去。我威胁了他一顿,然后在汽车后镜里看着他抽抽噎噎地穿过大街,往学校的方向去了,毕竟不放心,又掉转车头,开到他的学校门口,没有他的影子,不知道他是进去了,还是真的赌气回家去了,只好又开回家,没看到他,这才一路狂奔地往公司赶。
走到半路,象无数次的往常一样,满腔怒气慢慢消去,后悔一丝一丝地爬上心头:很久以来,我就经常暗自告诫自己不能跟孩子发脾气,特别是早上,一定要避免让他们怀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家——人生多苦啊,能给孩子们多少快乐就赶紧给他们吧!况且,谁知道,每天我们离别以后,是不是能够再见?
在我学经济的班上有个年轻的女孩子Anika,纤细修长,有一双敏感的大眼睛,平常闲聊的时候她每每说到一个叫“Tim”的孩子。Tim只有7岁,听上去非常调皮,我一直以为他是Anika男朋友的孩子,后来才听说他其实是Anika的弟弟,两年前他们父母先后病逝,Tim就和Anika一起住了。Anika经常说:离开家的时候,别忘了说再见;说再见的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爱人一个吻。
小时候我父亲教育我们,不论回到家还是离开家,都必须跟父母“打招呼”。我们家“打招呼”的方法,回家是叫一声爸爸妈妈,离开家则是叫一声爸爸妈妈再加上一句“我走了哈。”在我家的语言环境里,很少有“你好”“再见”这类温情脉脉的词汇,以至于当我在同学家里听到她们姐妹间相互说“请”的时候,心中无比羡慕。我的同学是北方人,我小时候认为:“请”和“对不起”这些词,只有用普通话说出来才相称,才不显得“假”,就象我同学家里人那样。而四川话是一种生硬的大众语言,似乎只适合在夏天黄昏时候,站在阳台上扯开喉咙高喊:二娃,回来吃饭啰!
我的少爷出身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往“大众”的堆里靠拢,实际上他这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后来我们一起在德国的街上听歌手献唱,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居然是歌手们收到路人的捐赠之后大喊的那声“谢谢”,他觉得那句话用德语喊出来尤其显得诚恳而有气魄。
如今我和我的孩子们讲德语,这门外语有时候就好像一幅面纱,把我安全地遮挡起来。我们说“请”“谢谢”“你好”“再见”,但是我不会对他们说“我爱你”,即便是用德语,我也说不出口。在我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曾经不断地对不同的人说过这句话,有普通话,有广东话,还有英文和德文,实际上,与其说我爱上是这句话的听众,还不如说我爱上了这句话--年轻时候的爱情更象一场场情景剧,我们都在按部就班地表演某种角色,有些话,作为台词来朗诵要比真实的表白容易得多。我从来没有用四川话说过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对我父母说过这句话,就象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一样。我是我父母的女儿,我们都不会用这么直接的语言来表达情感。
现代人类学家认为一个人童年时代的经历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他会用父母对待自己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我小时候,经常发誓以后要“不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现在当我痛斥大黑二黑的时候,一瞬间会恍惚以为对面棕色头发的小朋友就是我当年胖乎乎的弟弟,在我的德语腔调下面,我听到的却是当年我父母的声音。这种发现让我心灰意冷,即便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父母身上也无法改变我的沮丧:当年我父母在责骂我们的时候是否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子?
我是个记仇的人。实际上,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普通的中国父母,我成年之后,跟朋友们谈论起小时候挨打的事情,才发现我这个年龄的人,没有挨过打的实在是少数。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父亲用一根烧火用的木头棍子责打我七岁的弟弟,居然把棍子打断了。我弟弟在十几年前离家出走,我一直以为这件事跟我父亲有关,我也因此一直不愿意原谅他--但是究竟是不愿意还是不能,其实我也不知道。在二娃出走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责任都在我父亲身上,我自己真的就会更安心吗?
有的人类学家认为:影响一个人做决定的因素有三个,最基本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然后是他从童年的经历所得出的直觉经验,最后才是他成年后积累的社会经验。我父亲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也曾经试图关心过我弟弟的学习成绩,但是这种关心最后总是不得善终。二娃初三那年,因为没有考上重点高中,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上技校,一是上普通高中,最后多半仍然会落到技校。我曾经试图说服我父亲让二娃补习一年重新报考重点高中,因为一旦进入重点高中就基本上等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但是我父亲说:每个人的路都要自己去走。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避免对他这句话的怀疑,我怀疑这冠冕堂皇的道理后面其实掩藏的是他的软弱和怕麻烦。
大黑上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认为他与众不同,建议我们带他去做智力测验,如果他真是超智儿童,就应该送去本地私立学校的超智班。我没有带大黑去做过这种测验,这个故事我对别人得意洋洋地诉说过无数次:我只希望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过一种普通快乐的生活。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借口?而这个借口也只不过是披着另一种冠冕堂皇而已。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即使我心底里清楚,我最憎恶,批评得最厉害的那些东西,其实正是存在于我性格中而不愿意被我承认的东西。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一切,包括他自己。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人,是因为我知道我即使能够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我自己。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我面临的选择,一是跟我的敌人无休止地打斗下去,一是跟他握手言和。但是这两样我都不想选择,这是因为我虽然已经不再年轻,却也还没有老透。不再年轻,所以害怕两败俱伤;没有老透,所以不能甘心。
那些人类学家又说: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部分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一个人的基因是决定个人命运的重要因素。
你能够改变你的基因吗?
但是科学往往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真理。大黑刚刚出生的时候,最前卫的育儿手册上写道:培养孩子的独立个性要从婴儿时期开始,所以孩子哭闹时不能即刻抱他们。我至今能够看见当年的自己,咬着牙,蒙着耳朵,心乱如麻地坐在客厅的一角,卧室里,大黑在他的小床上无助地哭泣。大黑是个敏感的孩子,很多时候,我直觉到他的性格里多少欠缺一些安全感。但是,即使我在他婴儿时期曾经温柔地呵护他,如今他的性格真的会有什么不同吗?假设一个人的命运由性格决定,而性格由基因决定,就是说:无论你在最初选择了A还是B还是C,你最终的结局总是X。原来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人生就是由必然组合而成的必然。
我父亲现在已经老了,以至于每次见面,我都会对他心生怜惜,我知道他的怕麻烦并不只是对于我们,他自己病了,最多也就是到药店去随便买点胃舒平和感冒清,但是我小时候严重贫血,他曾经每天带我去医务室打针,让我骑在他肩头上回家。他也曾经为了给我买一本“安徒生童话选”,挤在人群里被偷去全家一个星期的菜金。在我出生之前,我父亲必定曾经欣喜万分地期待我的到来,就像我当年对于大黑的期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必定经历过无数的欣喜悲哀,得意失意。就像如今我在我的孩子们身上经历到的那样。
但是多少年来,我对于我父亲的记忆,更鲜明的却是另外一些片段。我一直在这些片段里挣扎,没有片刻的安宁。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之所以我对于这些片段念念不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血液里,我父亲的暴躁也是我的暴躁,他的顽固也是我的顽固,我的反对传统其实就是反对自己,而我对温情的嘲笑只不过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天生的羞怯,我和我父亲的战争,其实就是我和我自己的战争。
大黑渐渐长大,脾气也象我一样敏感易怒。因为爱他,我无法原谅自己;因为爱他,我不得不原谅自己。当他长大以后,对于他的母亲,我的记忆,也会象我对于我父亲一样吗?血脉长传,我感故我在。我一辈子都在自己感情的缝隙里求生,饱受折磨。我的孩子,但愿你因为也承袭了你父亲的血脉,不再经历你母亲那场无休无止的自我之战。